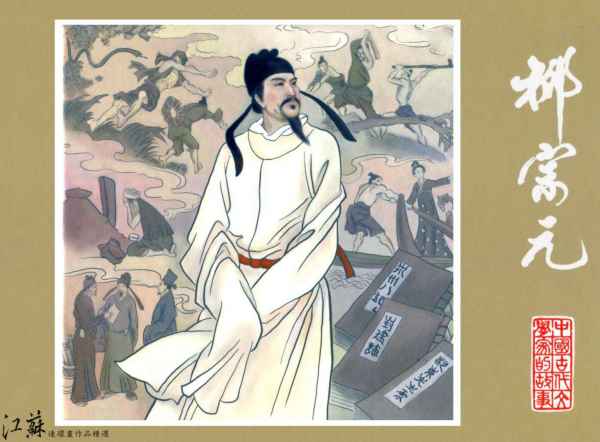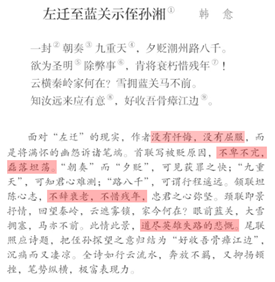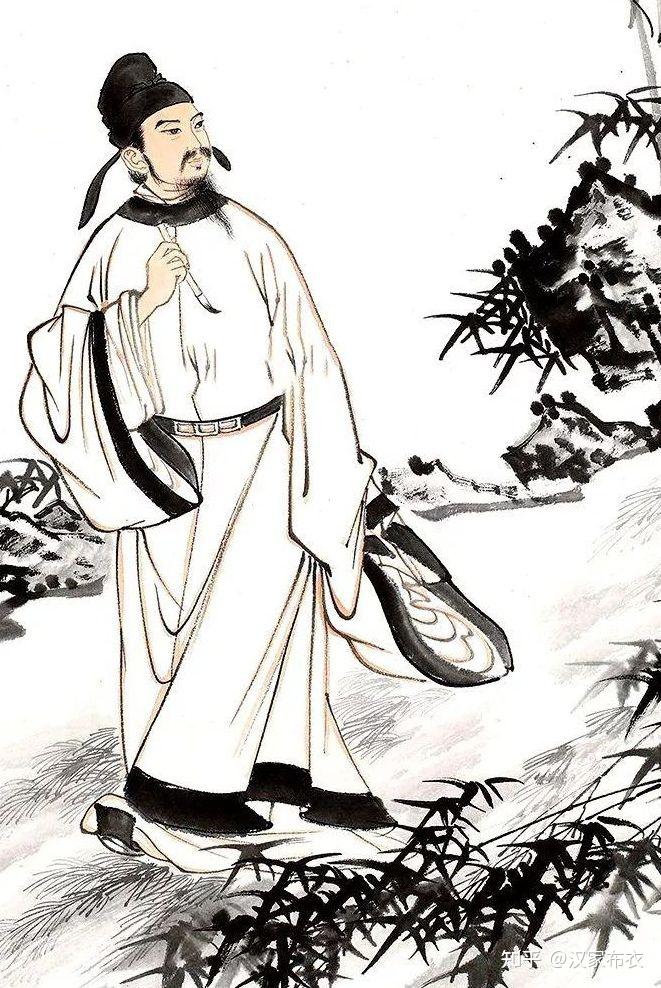Originally published at: 批判韩愈及其反动作品三篇 – 曙光
批判韩愈及其反动作品三篇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儒法斗争,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内重要的两条路线斗争、是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至今仍有其深刻影响。社会主义中国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发现了一条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凡是反动的阶级——没落奴隶主阶级、大地主阶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总是尊儒反法,鼓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实行复辟倒退;凡是进步的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尊法反儒,主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行变法革新。然而,自1976年资本主义复辟后,中修叛徒集团却极力抹杀儒法斗争这一历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为了维护自身腐朽反动的统治,将历代反动阶级奉为圭臬的儒教重新捧上台面,为儒教人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大肆宣扬“师道”、“孝道”、奴才之道,利用儒教在精神上奴役人民。韩愈,就是中修所鼓吹的儒教人物中的典型。中修把韩愈捧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肉麻地吹嘘他“有思想、文章,更有事功”。在中修的语文教科书中,韩愈的《马说》、《师说》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更是被列为必背篇目,流毒甚广。接下来,我们便从韩愈的这三篇作品入手,彻底揭露韩愈的真实面目,看看究竟什么是他的所谓 “思想、文章和事功”。这对于我们认清中修如何利用儒教麻痹青年,是很有意义的。
韩愈生活的时代背景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无向辽东浪死歌》)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衣冠殄丧,法众消亡”。农民起义基本打垮了魏晋兴起的门阀士族大地主势力,山东一带起义军还提出了“严惩腐儒、禁绝儒学”的革命口号,他们直捣孔府、焚烧儒家经书,对大地主阶级借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儒教造成了沉重打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唐朝以李世民、武则天为代表的法家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其中,以庶族出身的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最为彻底。在经济上,她通过抑制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维护均田制度,使唐朝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在政治上,她多次削平宗室、贵戚和上层官僚的叛乱,继承先秦法家“以吏为师”的主张,委派具有法家思想的官吏担任太学祭酒,一切政事“不问诸儒”。然而,尽管庶族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但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利益始终是与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为了维护统治,他们同样需要以某种反动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武器,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唐朝统治者主要利用的是佛老思想,儒教并不受到重视。历代皇帝往往大兴佛寺,并赐予其大量土地和免税特权,由此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大土地所有制——寺院庄园,以及一批新的大庄园主——僧侣地主。并且,以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即天宝年间为转折点,随着中小地主阶级向他们的反面转化,即通过不断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阶级,唐朝前中期执行法家路线的成果——均田制、府兵制一一走向崩溃。此后,一面是以浙东袁晁起义为代表的、由沉重的剥削所激起的农民阶级的不断起义,一面是以安史之乱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的连续混战与叛乱,唐朝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在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发起了一场以削减租赋进奉、罢免权贵宦官、任用革新人才、夺取阉党兵权为内容的永贞改革。然而,儒教的卫道士、大地主阶级的乏走狗韩愈,此时却极力攻击改革运动、对革新派口诛笔伐,并编造所谓“道统”说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力图“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1]。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韩愈先后炮制了他的三篇反动文章。
宣扬“读书做官”论、对权贵舐痈吮痔的《马说》
古文运动的投机者、永贞革新的反对者、大地主阶级的乏走狗韩愈《马说》创作于795年至800年间。如前所述,此时正值宦官擅权跋扈、节度割据混战的国难之际,泾源兵变(783—784年)才过去不很久、宫市使也还在毫无止境地刻剥人民。然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却一门心思投机钻营,绞尽脑汁地为自己寻得一个进身之阶、荣身之计。他三次参加吏部考试,三次不中;又三次上书宰相、三次拜访宰相官邸,阿谀奉承、卖惨哭求,肉麻地将对方捧为“一饭三吐哺”(《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周公,甚至不惜自比“管库”、“盗贼”(《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希望得到当权者的赏识,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于是,韩愈眼见“此路不通”,便转头卖身于藩镇割据势力,先在宣武节度使董晋手下做观察推官。董晋死后,宣武军立刻发生兵变,韩愈在一片混乱中慌忙逃窜,又跑到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帐下做节度推官。然而,张建封不久又病死。于是,失去了靠山、像他的祖师爷孔丘一般“累累若丧家之狗”的韩愈,便在这时抛出了《马说》,一面无耻地吹捧自己、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恨,一面对权贵俯首帖耳、献上一纸表忠心的投名状。
《马说》开篇的第一句话——“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便暴露出韩愈世界观的极端唯心主义。在他看来,先有能够识别千里马的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先有对事物的认识或认识事物的能力,然后才有事物本身。一定的思想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韩愈拼命夸大“伯乐”的作用,甚至不惜脱离现实,实际上不过是奴颜婢膝地向权贵表白心迹——像他这样的腐儒,只有仰仗“贵人”的赏识才得以荣身。韩愈在一句话后接着说:“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说明在他眼中,只有“伯乐”一类天才人物才能识别“千里马”,而与养马实践联系最紧密的“奴隶人”——马夫却根本不能认识。韩愈极端鄙视作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主体的劳动人民,但他自己又是什么货色呢?韩愈无耻地吹捧自己“有千里之能”,之所以“才美不外现”、甚至“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只是因为“食不饱力不足”,只要能够一顿吃上“一石粟米”,便能大显身手。实际上,韩愈连他自己奉为“道统”的孔孟之道也并没有读过多少。在《韩愈全集》中,真正“扶道助教”的,只有《原道》等寥寥数篇而已,其余几百篇尽是些吹拍文章。并且,韩愈在生活作风上也极端腐朽,黄、赌、毒俱全。他在《酒中留上襄阳李相公》中曾情不自禁地记述到自己通宵达旦饮酒狎妓的劣迹——“耳热何辞数爵频”、“金钗半醉座添春”,简直是无耻至极!嫖娼既已如此,赌博更是常事。就连韩愈的好友、同为儒生的张籍也写信奉劝他:“博塞(一种赌博游戏——引者注)之戏与人竞财……君子固不为也。今执事(指韩愈——引者注)为之,以废弃时日,窃实不识其然”(《上韩昌黎书》),希望韩愈能专心著书立说、复兴孔孟之道。而韩愈却对此推三阻四,说是等到五六十岁时再写也不迟,结果直到死时也没有完成自己发宏愿要写的《论语注解》。至于吸毒,同时代的白居易在《思旧》中记载道:“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痊”,韩愈晚年幻想能够实现永生不死,竟然服食“金丹”——硫磺,最后还因此丢了老命。可见,韩愈一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也不懂的儒教徒根本不是什么“千里马”。而中修对韩愈的百般粉饰,只不过是以功名利禄引诱青年,教他们走上个人成功的资本主义邪路,教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尊严和良心、在资产阶级面前学着韩愈一般摇尾乞怜罢了。
维护“师道尊严”的《师说》
《师说》创作于801年至802年。此时正值永贞改革前夕,地主阶级革新派已经在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做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王叔文“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九》),成为改革运动的骨干;柳宗元在799年作《辩侵伐论》,主张坚决镇压淮西节度使叛乱,得到太子李诵的重视。革新派的政治活动卓有成效,柳宗元在长安时,“日或数十人”(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向他讨教革新道理,“一时辈行推仰”(《新唐书·柳宗元传》)。儒教在唐朝本就不受统治者重视,此时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法家思想的流行更加式微。见到此情此景,作为孔孟忠实信徒的韩愈心急如焚,在当上国子监四门博士后便立刻抛出《师说》,大叫什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企图恢复儒教的那一套师生等级制度,号召人们尊孔读经,用复古、倒退的孔孟之道束缚人们的思想,以达到阻止法家实行政治变革的目的。
《师说》劈头便写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对于这一句话,中修一般将其翻译为“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的人”。然而,如此一来便掩盖了韩愈的反动政治目的。韩愈亲口承认:“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即是说,他口中的“师”指的并不是传授一般文化知识的人,而是所谓“传道”者。这个“道”具体来说又是什么呢?韩愈在他的《原道》中做出了回答——“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令而致之民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可见,“道”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孔孟之道,就是地主阶级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统治人民的封建秩序。为了维护“道”的权威,必然要求“道”的传授者——“师”也具有权威。这便是韩愈作《师说》的险恶用心——为“师”加上一圈神圣的光环,通过宣扬“尊师”进而鼓吹“重道”。
韩愈是如何论述“从师”的必要性的呢?他写道:“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这两句话乍看起来是很有迷惑性的,表面上说人们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甚至进一步“否定”了儒教圣人孔丘的“天才”,好像是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但实际上,韩愈在这里鼓吹的仍是天才论和先验论,只不过是采取了更狡猾、更隐蔽的形式而已。韩愈在《原性》中重新咀嚼董仲舒所提出的反动“性三品”论道:“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也就是说,所谓“性”是与生俱来的,“上品”的人生来就是善的,“下品”的人生来就是恶的;只有“中品”以上的人才能够通过后天学习而更加明白天理,“下品”的人是不能通过教育改变的,因此只能用暴力统治他们。可见,韩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所说的“下品之性”,与孔老二所说的“下愚”、董仲舒所说的“斗筲之性”一样,都是极端污蔑和鄙视劳动人民的。韩愈之所以要为他的先验论、天才论披上一层唯物主义的外衣,实际上只是出于在当时具体社会条件下复兴儒教的需要:由于“师道”,即孔孟之道已经不传,自然就不可能再片面地强调“生而知之”——如果有人生来就懂得孔孟之道,那么就用不着再学习了。相反,只有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才能够吸引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投入他的门下,才有可能使儒教思想打败佛老思想和法家思想、重新恢复统治地位。并且,韩愈还无限夸大间接经验的作用,认为人们只有通过“从师”才能学到知识,否则只能落得个“愚益愚”的下场。他否认三大实践是人们一切认识的来源,实际上是根本反对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
韩愈又是怎样美化儒教的师生等级关系的呢?他接着写道:“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同样是具有欺骗性的一句话,似乎韩愈是反对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而主张以“贤者”为师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韩愈恰恰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忠实捍卫者。在这里,他只不过是再次强调“师”的权威是“道”的权威所赋予的罢了。韩愈本人出身于中等地主阶级家庭,并且在写下《师说》时也不过是国子监中的一名从七品的小学官,而当时的太学学生却多来自于世家豪族——“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状》),自然看他不起,更加不可能屈尊敬他为师、向他学习孔孟之道。于是,韩愈便鼓吹起这样一套貌似不看等级出身、只看“闻道先后”的师道观,希望能够有利于他吸引世家豪族子弟到自己门下,从而一方面宣扬儒教,一方面利用师生关系为自己扩展人脉、打通一条通往高官厚禄的门路。韩愈口头上讲什么“无贵无贱”,但实际上像他一样的儒教“禄蠹”们正是最热衷于攀附权贵的,当时的一句话便道出了实质:“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你们年龄相近,在儒学上的“造诣”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又何必要搞那一套师生名分呢?之所以一定要这样,无非是为了趋炎附势,耻于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而又阿谀奉承地拜地位高的人为师罢了。正是因为这句话揭穿了韩愈一类腐儒们的丑陋面目,于是韩愈便恼羞成怒地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他恶毒地咒骂不遵从儒教师道的革新派还不如“君子”所厌恶的“泥腿子”,然而只是暴露出自己极端无能、无耻和反动的实质。韩愈猖狂地逆历史潮流而动、“抗颜为师”,结果只是落得了个可笑的下场。柳宗元在他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记载道:“世果群怪聚骂……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世人果然嘲笑和谴责他,韩愈因此被称为“狂人”,当他在长安时,连饭都等不及烧熟,就被皇帝赶出长安、下放到别处去了,像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许多次了。
杰出的地主阶级文学家、改革家与唯物主义者柳宗元中修之所以把《师说》收入教科书,并把韩愈打扮成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对者”,正是为了向广大学生灌输“师道尊严”的儒教观念,使他们成为对教师唯命是从的奴才。中修利用韩愈的这一套黑货极力美化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说什么教师的作用不仅是“教书”、更在于“育人”,让学生对比自己懂得更多文化知识和“做人道理”的教师俯首帖耳。实际上,所谓“教书育人”,不过是在教学生“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的同时,还让他们学会服从于剥削阶级的统治,中修的这一套“园丁”说完全是一千二百多年前韩愈“师道”说的翻版。中修在口头上讲什么“师生平等”,但实际上在中国从来都是教师压迫学生,从来没有学生能够与教师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教师残酷迫害学生、造成学生伤残死亡或心理创伤的悲剧比比皆是。中修极端野蛮而又十分普遍的“衡水式”学校,正是韩愈所谓“师道尊严”在今天的活标本!
中修为了宣扬儒教极力“崇韩贬柳”。然而,柳宗元与韩愈针锋相对的法家教育观点才是真正具有平等色彩的。对于师生关系,柳宗元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反对儒教的师生名分和师生等级制度,只要双方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交互为师即可。他认为,教师要尊重学生——“不敢倦(懈怠),不敢爱(吝啬),不敢肆(放肆)”(《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而学生也不应该对教师迷信盲从,应该常常提问:“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无曲乎?”((《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于择师的标准,柳宗元则将是否懂得法家革新之“道”放在第一位——柳宗元所说的“道”与韩愈是根本不同的,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儒教复古倒退的“圣人之道”、孔孟之道,认为它“不益于世用”,主张实行“以生人为主”(《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即服务于现实的“生人”和时事的“道”。从这一点出发,柳宗元与韩愈在对待劳动人民和达官显贵的态度上也是根本不同的,他说:“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 师友箴》)——对于地位低微的仆人和乞丐,如果他们具有革新思想,那么也应该以他们为师;相反,即便是王侯公卿,要是他们不懂得改革的道理,也要跟他们离得远远的。柳宗元还提出“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读书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以所学“用于世”,即对时政有所帮助、对社会发展有所推动。可见,柳宗元的法家教育思想与韩愈的儒家教育思想对比,高下立判。
鼓吹“忠君爱国”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写于819年。当年,韩愈上书反对唐宪宗李纯迎佛骨入宫,结果引起李纯大怒,险些惹上杀身之祸,最终被贬潮州。正是由于谏迎佛骨案,资产阶级文人常常将韩愈吹捧为“直言敢谏”的“反佛斗士”,给他套上一个又一个反对宗教、忠君爱国的“进步”光环。然而,鲁迅说过:“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2],韩愈用以“反佛”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同样腐朽反动的“君臣父子”、孔孟之道。并且,思想文化上的斗争是一定阶级或阶层间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反映,韩愈正是从世俗地主的利益出发“反对佛教”的。前文已经提到,由于唐朝统治者主要以佛老思想作为麻痹人民的精神武器,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势力极大地发展起来。他们凭借着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与世俗地主展开了激烈的对土地和劳动人口的争夺。韩愈在《送灵师》中便写道:佛教的泛滥造成了“齐民逃赋役”,“耕桑日失隶”。当然,韩愈作为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并不在乎封建国家的利益。在这里,他只是以仓廪空虚、无人应役的现实劝谏统治者采取贬斥佛教的政策而已。可见,韩愈的所谓“反佛”,并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而只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3]罢了。
韩愈的个人活动,更是证明了他不仅不是宗教迷信的反对者,而且还是它的忠实信徒。在被贬潮州路过岳阳时,韩愈到黄陵庙做祷告,祈求神灵保佑他早日遇赦回朝。在潮州做刺史时,韩愈更是上演了一出“祭鳄鱼”的丑剧,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写了一篇《祭鳄鱼文》。820年,唐穆宗李恒即位,韩愈遇赦归京,但他却认为这是自己的祈祷得到了应验,于是便捐献“私钱十万”重修黄陵庙,并特地为此写了一块《黄陵庙碑》。并且,韩愈还与各种和尚、道士私交甚密,肉麻地吹捧他们为“高僧”,“又作为诗歌以光大之”。
揭穿了韩愈“反佛”的实质,我们回到原诗中来。《左迁》全诗如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名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一遭贬官,韩愈便顿感世事无常、仕途一片黑暗,自己这把老骨头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一再叮嘱侄儿为自己收尸送葬。同时,他还不忘自我吹嘘一番,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敢于“死谏”的大忠臣,俨然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然而,一到潮州,韩愈马上又写了一篇《潮州刺史谢上表》向统治者摇尾乞怜,又是为昏庸无能的唐宪宗李纯歌功颂德,又是将自己的上表说成是“狂妄戆愚、不识礼度”、“正名定罪、万死犹轻”,一连使用四个“顿首”(磕头),恳求宪宗对他“哀而怜之”。“视死如归”的“忠臣”形象荡然无存,厚颜无耻的奴才嘴脸跃然纸上。但是,中修却闭眼不看这篇黑文,硬说什么《左迁》表现了韩愈的“刚正不阿之态”和“英雄失路之悲”,可与《谏佛骨表》合称“双壁”。可见,为了替大地主阶级的乏走狗韩愈辩护、为了宣扬“忠君”即顺从于统治阶级的儒教奴才思想,中修已是黔驴技穷。
柳宗元的战友刘禹锡同是被贬,刘禹锡展现出的精神便与韩愈截然相反。然而,这也被中修崇韩贬柳、贬刘的反动宣传所埋没了。与柳宗元一样,刘禹锡同属革新派的骨干,在永贞改革失败后受到反动势力迫害,屡遭贬谪。821年,刘禹锡被贬夔州,这已经是他自改革失败十六年以来的第三次被贬。但是,刘禹锡并没有悲观失望,他在第二年创作了著名的《浪淘沙·其八》:“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不要说保守势力的诽谤攻击像恶浪一样翻滚,不要说遭到贬谪排挤的革新志士会如泥沙一般沉沦;千遍万遍的过滤虽然艰难辛苦,但只要淘尽泥沙总能得到黄金!与韩愈不同,在遭到贬谪后,尽管面对着一时甚嚣尘上的强大敌人,刘禹锡不仅没有乞怜求饶、更没有放弃自己的革新理想,反而更加坚信改革在经过艰苦的斗争后一定会胜利。在刘禹锡的许多诗句中,我们也都可以发现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836年创作的《酬乐天咏老见示》中,刘禹锡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种老当益壮、坚持战斗的意志,不能不令一遇挫折就大喊大叫什么“吾命休矣”的韩愈相形见绌。
列宁说过:在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下,“工农的年轻一代……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4]中修将韩愈的三篇反动作品编入教科书,目的正在于将青年学生塑造成这样的奴仆——他们教育学生:只有功名利禄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最短捷径,便是借“伯乐”、“贵人”即统治阶级之手鲤跃龙门、一飞冲天,因此必须有一套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夫(《马说》)。这种功夫又从哪里来呢?他们回答:只有从书本来、从学校来、从教师来,为了“前途”着想,学生只得老老实实地读书、规规矩矩地服从学校的制度、恭恭敬敬地向教师讨教(《师说》)。然而,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光有能力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一颗“忠心”。于是,中修又跳出来说:只有奴颜婢膝、逆来顺受,才能使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诚意”、才能受到他们的青睐(《左迁》)。中修满心以为这样就能使青年全都成为“遇见所有的富人都驯良”[5]的好奴才、乏走狗。“但是,学生们的身上还潜藏着转变的希望、革命的希望。随着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小资产阶级之间互相竞争的现象日益激化,家长和学校对于学生的压迫就愈加沉重。这必然会激发学生们对于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不满,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满,引起他们的思考。”[6]即便中修费尽心机地想要毒害青年,但资本主义的危机必将爆发,青年们的觉醒也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