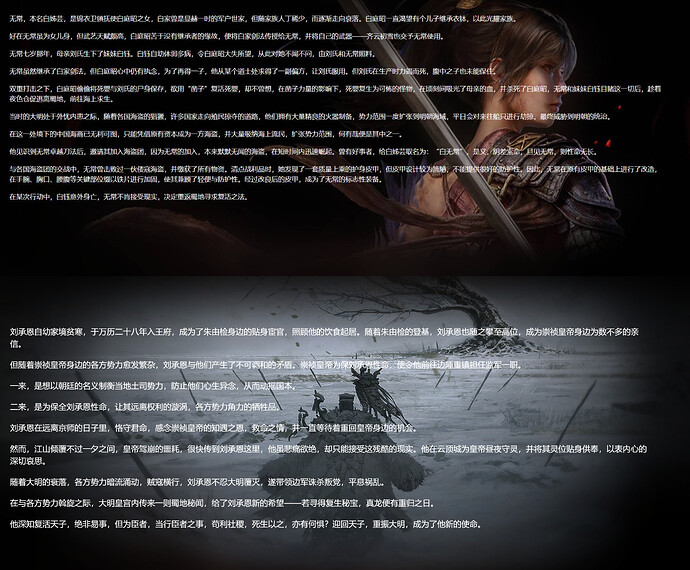编者按:近来中修出现了一款以明末为背景的资产阶级电子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引发了激烈讨论。这款游戏内容十分反动,女主角出身于反动锦衣卫家庭,常年与“海商”(即倭寇)为伍,后来又在四川地区疯狂屠杀当地人民和农民军,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在这款游戏中,女主角将明朝大地主、农民军和流民等汉人当作敌人,将张献忠的三个没有降清的义子当作敌人,却将降清的孙可望设定为“中立NPC”,在历史上的明末时期疯狂屠杀人民的清军也从未出现在游戏中。很多“皇汉”分子出于大汉族主义思想,反对游戏中不出现清朝,却将明军作为击杀对象的情节设计,但是实际上,这款游戏也疯狂美化明朝地主阶级,和“皇汉”分子崇拜地主阶级的思想别无二致。它用“立体人物”的手法来塑造明朝地主阶级,胡说他们虽和女主角所处阵营不同,但是也是”忠诚”、“爱民”的,而却对张献忠以及他所领导的大西军极尽丑化之能事,污蔑大西军是“强盗”,是造成四川动乱的“祸首”,将农民领袖张献忠设定为所谓的“通关boss”,无耻地将满汉大地主掳掠、屠杀四川人民的累累罪行,都推到让农民翻身的大西军头上!为了彻底批判这款反共反人民、吹捧满汉封建主的反动游戏,还明末农民战争的本来面目,现经编辑部同意,编者将《曙光》杂志第六期中的一篇讲述明末农民起义的文章单独发布出来,供大家阅读参考。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的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1]明末清初便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农民革命战争时代。明末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得广大劳动农民陷入贫困、奴役、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觉醒了的农民大众拿起武器、举起义旗,在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领导下一步步实现“均田免粮”等社会要求,猛烈冲击明朝的反动统治和孔孟之道,最后亲手将妄图暴力压制他们的崇祯王朝彻底埋葬,把封建统治者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彻底粉碎。然而,长期以来,英勇的农民领袖和农民革命军被地主资产阶级恶毒地咒骂为“愚昧无知”、“杀人狂魔”,最后必定会“奢侈腐化”,遭到失败。革命不容污蔑、历史不容颠倒,新中国建立以后,劳动人民第一次掌握了政权,将地主资产阶级强加给农民阶级的冤案翻了过来。而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走狗文人又大搞历史唯心主义和英雄主义,大肆鼓吹帝王将相之家史,对革命农民和农民革命又是大加污蔑攻击。如今,我们革命者就要将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强加于农民阶级头上的污名去除,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愚昧无知还是聪明正直?
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的很多人,想必都听过资产阶级对农民“愚昧无知”的污蔑之词。中修头子习近平,曾污蔑农民因为愚昧无知而受穷受苦,狂妄地声称“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2];像王福重这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肆无忌惮地辱骂农民“懒惰愚蠢,不值得尊重”;为中修效犬马之劳的教师,为达到欺骗、奴化、控制学生的罪恶目的,也常将“不好好学习之后就是去种地”挂在嘴边,将农民贬低为“愚蠢而无能的低贱之人”;历代反动地主阶级,也遵奉孔老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3]的衣钵,理应剥削这些“与禽兽无异”的农民。“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4]明末农民起义军以铁的事实,粉碎了几千年来地主资产阶级关于农民阶级、劳动群众“愚昧无知”的无耻谰言。明末农民起义军,不同于任何地主阶级分子,是旗帜鲜明地、坚决地反对儒教和封建迷信,宣传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敢于反抗封建统治,要求消灭贫富悬殊,追求平等平均。
在起义之初,民间就流传着一首名为《塌天歌》的歌谣。明朝地主阶级极力推崇程朱理学,制造三纲五常就是“天”、“富贵由来自有天”[5]的歪理邪说,要求人民要“顺天知命”,安于君主对臣民、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统治。而人民通过被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亲身经历,认识到了“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的社会黑暗现实,识破了地主阶级炮制的“天命论”谎言,喊出了”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的塌天口号,批判了反动的程朱理学,传达了广大人民对腐朽的封建统治的无比愤恨。《塌天歌》表现出的反天命的战斗无神论思想,正是明末农民革命的鲜明特点之一。革命农民不利用任何宗教思想来作为斗争手段,抛弃一切宗教外衣,直接面对社会矛盾,提出“均田免粮”,“除暴恤民”的革命纲领,制定“据中原、取天下”的战略计划,以推翻明朝的封建统治。“均田免粮”是农民革命的经济纲领,直指封建制度的核心——封建土地所有制,表现出明末农民革命把历代农民起义的“平均”、“平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过往的农民起义,至多提出“均贫富”,着眼于钱粮等生活资料的均分,而明末农民起义适应农民抗租夺地的斗争浪潮,提出平分土地的要求。这是“历经千辛万苦并经过多年压迫所锻炼出来的要求”[6],而这种要求体现的思想,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7]。“除暴恤民”是农民革命的政治纲领,体现了农民的阶级原则,要除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要关心、保护广大劳苦人民的切身利益。“据中原、取天下”是农民革命的战略思想,把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全国政权、用农民阶级专政代替地主阶级专政作为自觉的革命目标,这同样也是过往农民革命未明确提到的。“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8],明末的革命农民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有夺取政权,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9]。农民军在革命纲领的精神感召下、在领袖李自成“闯”字的战旗下,敢闯敢干,用实践冲破程朱理学的反动说教。李自成农民军每到一处,把“均田免粮”的斗争纲领不同程度地予以实现,力图建立一个使贫汉“都欢悦”的理想社会,向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宣战。农民军“不杀平民唯杀官”,镇压曾经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如在洛阳,就惩杀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福王朱常洵,大灭地主阶级不可一世的威风。此外,农民军还发动广大农民也“瓜占”地主的田产、牛只,一度出现“奴(佃农)坐于上,主(地主)歌于下”的生动局面,用行动表明了矛盾双方的地位是可以转化的,用朴素的辩证法否定程朱理学“定位不易”的形而上学观点。农民妇女也被发动起来投身革命斗争,如李自成的高夫人就是农民军的妇女领袖,对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粉碎了“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农民军也在李自成的带领下,烧孔庙、砸程祠,最后杀进北京,夺了崇祯的权,推翻了反动的明王朝,破除明统治者编造的“承天应运”的神话,证明“三纲五常”根本不是“天理”,人民受苦受难根本不是“天命”,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否认了程朱理学反动的客观唯心主义,砸烂了程朱理学这个精神枷锁。李自成是明末杰出的农民领袖,是农民阶级的优秀代表。他从小便在生死线上受煎熬,二十三岁主动投身农民革命,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成长为卓越的农民革命家,最后在三十九岁时为农民阶级的革命事业壮烈牺牲。李自成的革命哲学,集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进步思想。李自成站在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上,自觉运用劳动人民所固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其中所表现的认识原则和思想方法,同样也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李自成基于唯物主义的认识原则,从社会实际出发,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痛苦不堪正是地主官僚霸占着土地,掌握着政权、对人民进行压迫剥削的结果;李自成也提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革命的“顺逆观”,地主阶级大骂农民革命军为“逆贼”,而李自成将农民革命政权的国号定为“大顺”,农民阶级政权取代地主阶级政权即为“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李自成在攻克北京后,看到“承天门”大匾,对准“天”字,弯弓怒射,表现出反天命的无神论思想的战斗风格;李自成在领导作风上注重集思广益,进行调查研究,从不主观臆断行事,这种革命实践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为李自成指挥百万农民军取得赫赫战果提供了世界观基础。
现代资产阶级特别喜欢打着“科学”的幌子污蔑农民起义“迷信宗教”,但实际上,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革命农民“不信天命信革命”,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作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天,而是相信依靠自己就能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相反,此时地主阶级还在搞“顺天”、“承天”、“知天”,极力吹捧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也是宗教,只不过是它把作为人格神的上帝换成了无意识的“天”而已,还是一样地宣扬蒙昧主义。明朝统治者大力宣扬儒教,以至于“天下庙祀,凡一千五百六十余处。每岁春秋二祭”[10]。此外,明朝统治者还利用其他许多宗教麻痹人民,从朱元璋和朱棣时期就开始宣扬佛教、道教,后来还兼有伊斯兰教等,各种寺庙相当兴盛。相形对照之下,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到底是谁聪明、谁愚昧就很明显了。即便是法家地主阶级,其思想也没有农民阶级思想那般富有革命性。拿中国的“文艺复兴三杰”——李贽、黄宗羲和王夫之来说,即便是以反儒著称的李贽,还要给孔老二说上两句好话,没有也不可能像农民军那样烧毁孔庙程祠,否定儒教的道德观和等级制;即便是以批判君主专制著称的黄宗羲,搞得还是剥削阶级内部贤人政治那一套,没有也不可能像农民军那样起兵反对明朝封建专制统治,最终埋葬了腐朽的崇祯王朝;即便是以朴素唯物主义著称的王夫之,在历史观上仍然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没有也不可能像农民军那样不畏天命,用自己的双手来改造这个社会。更何况,法家地主阶级能获得一些正确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要依靠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农民阶级根本不是“愚昧无知”,而是真正的聪明正直。
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总是污蔑农民“愚昧无知”,觉得自己这种高贵的读书人比没有接受多少科学文化教育的泥腿子们优越一千倍。这种言论既愚蠢又反动。“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11]真正的知识不是从地主阶级脱离实际的反动经书、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的反动教学课本中获得,而是从实践中获得。地主资产阶级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什么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天才”,但只不过是蠢材。劳动人民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有最多实际的经验,而最少剥削阶级的偏见,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也是如此,明末的革命农民便也证实了这个真理。况且,无论是过去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还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农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不能获得剥削阶级所谓的“高等教育”,不就是因为剥削阶级对他们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吗?而剥削阶级之所以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不就是因为他们吸食了包括劳动农民在内的人民的血汗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现代资产阶级重弹农民“愚昧无知”的老调有其险恶的阶级目的。在历史领域,资产阶级污蔑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愚昧无知”,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为他们的老前辈地主阶级吹牛拍马,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制造“合理”根据。他们污蔑古代的农民,也是在污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农民。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了最为严重的城乡对立,资本家纵情享受的城市统治着衰颓破败的乡村,使得乡村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广大劳动农民(小农、农业工人)受着资产阶级的掠夺,如遭受产业资本家和商人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价”的方式剥削。资产阶级胡说现代的农民“愚昧无知”,就是要抹煞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根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资产阶级对于农村、农民的剥削,妄图以此谬论钳制劳动人民的思想,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杀人狂魔还是革命英雄?
在四川梓潼县大庙山风洞楼中,有一尊金脸绿袍的张献忠像。自17世纪以来,梓潼县劳动人民长期奉祀张献忠塑像,即便清朝统治者焚毁塑像、还写了一篇《除毁贼像碑记》,勒石建碑,镇压当地照管张献忠香火的裴、贾两家,劳动人民仍不屈不挠,针锋相对,重建了张献忠的塑像[12],以表达对起义领袖的尊敬和对封建统治的憎恶。张献忠这样一位被劳动人民永远怀念的农民革命家,却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口中被说成是“嗜杀成性、残暴不仁、屠戮四川百姓”的千古罪人、杀人狂魔,遭到了极为严重和长期的污蔑和诽谤。时至今日,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互联网忽然流行起了“张献忠”梗,以早已被证伪的“张献忠写《七杀歌》、立七杀碑”为代表的谣言层出不穷,针对所谓“张献忠屠川”的搞怪图片更是泛滥成灾。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左圈分子所制作的“张献忠屠川”图片中,往往是张献忠塑像和有关“屠杀”的文字的组合。劳动人民因爱戴革命领袖而建造的塑像,却成为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左圈分子嘲弄的对象;革命领袖与明朝封建统治者英勇斗争的事迹,被所谓“屠川”的谣言一笔勾销,一笔抹煞。历史真相不容歪曲,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劳动人民也决不同意!
资产阶级分子曾叫嚣:目前,有关“张献忠屠川”的史料多如牛毛,显然无法完全否定。他们自诩“公正客观”,“一切听命于史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然后便从地主阶级的文献史料中得出了“张献忠屠川”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史料是有阶级性的,地主阶级编写的史学著作,反映了地主阶级的阶级偏见,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现代客观主义者无论怎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超阶级的史学家,也难掩他们的历史科学的强烈的资产阶级党性,有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有党性的理论,但是它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3]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要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性和阶级性高度统一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洗刷掉地主阶级强加在张献忠的主观色彩,怎么才能去伪存真,探究出历史事实和本质?资产阶级这么热衷于那些反动地主分子编写的史料,那我们就看看,那我们就用阶级方法来去分析分析,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
张献忠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到大,他便一直遭受着地主恶霸、军中长官的欺压,过着被压迫、受歧视的生活,这在他心里埋下了对反动地主阶级分子的深刻仇恨的种子。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领导农民首先点燃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十八寨举行起义,将自己的余生都投入到解放农民的战斗中,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农民领袖。他领导农民军转战南北,向四川进军,吸引并且击败了明朝反动军队的主力。此后,他又向东进军,节节胜利,在1644年,转回四川成都建立了大西农民革命政权。资产阶级还狂吠什么张献忠是一个屠杀四川人民的恶魔,但是实际上,张献忠作为农民领袖和明朝反动军队作战,本身以及只能依靠的就是被明朝统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他根本不可能滥杀百姓,根本不可能对四川人民伸出血腥的屠刀。明朝反动军队进攻人民,依靠的是整个地主阶级以及封建国家机器,张献忠领导农民军推翻明朝的反动统治,依靠的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
“事实胜于雄辩”,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污蔑截然相反的是,他所领导的农民军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深受百姓的欢迎。张献忠在四川建国后,为了严肃军纪,曾颁布《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并且刻之于碑。此碑明文规定:“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守X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等等。毛主席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4]明朝末期,广大贫苦农民都挣扎在生死线上,他们没有或者很少有生产资料,两手空空,早就绝了发财的望。对于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他们的心中早就“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15],他们早就想打翻这个世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举行了起义,而每次起义的锋芒,都指向当朝的皇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起义农民军大公无私、舍生忘死的精神的直接写照。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也是如此。不只是张献忠本人,起义军战士们也都出身于佃农、贫农。他们都是最为善良的劳动人民,为了”勤民“、为了推翻这个不公的社会,才参加革命队伍、与明朝军队作战。张献忠和他所领导的农民军,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想要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明王朝,也在经济上想要通过实行“均田免粮”的政策来让农民翻身。在1640年,张献忠农民军进入四川,攻克大昌、巴雾口,袭击夔州山背,“自夔山后走,屯田涂二坝,打粮自给”[16],实现贫富均田。在长沙时,他颁发“钱粮三年免征“的檄文,并将明朝反动地主官僚、兵部尚书杨嗣昌所“霸占土田,查还小民”。1643年3月,他率领农民军攻下汉阳、武昌,逮捕楚王朱华奎,发楚王物资以赈济广大饥民。据记载,张献忠在四川建国后,也对边区少数民族有过“免其三年租赋”的政策。革命群众热情地拥护张献忠,大力支援农民军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张献忠和他领导的农民军才能大败明朝军队。在张献忠第一次进入四川,与杨嗣昌所领导的反革命军队作战时,农民军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避免同官军打阵地战,采取“以走致敌”的流动战术。当时的农民军轻装前行,到哪儿都能得到群众的粮食供应,有时一日夜骑马连走能走三百。而明军裹粮行军,根本无法追赶上农民军,完全陷入被动,最终为农民军所击败。在张献忠第二次进入四川后,百姓“应募入伍者,尚不下数万”[17],“喜于从贼”[18],四川射洪县“百姓开门迎贼”[19]。这些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地主资产阶级所谓“张献忠屠川”的谣言,证明了:农民军不是一支为了实现个人的荣华富贵,就去屠杀人民、掳掠财产的军队,而是一支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军队。
“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叛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20]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其他地方还是在四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城池后,确实使用了暴力,确实杀了人,但是他们使用的是革命暴力,是正义而且完全必要的。在明末,四川已经变成了一个“积愤不平,抑愤难诉、憾天沮地、泣鬼愁神”[21]的炼狱,当时的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一边是四川大地主官僚,过着穷奢极欲的吸血鬼生活,蜀王宫里堆金叠玉;一边是四川的贫苦人民,被强征数不清的苛捐杂税,“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而号寒”[22]。不畏强暴的四川人民,在张献忠入川建国之前,就已经发起多次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不幸都以失败告终。而在张献忠入川之后,张献忠实行剥夺剥夺者的政策,推动和影响全川人民进行“除五蠹”(衙蠹、府蠹、豪蠹、宦蠹、学蠹)的斗争,坚决打击地主阶级,惩杀反动分子。在重庆,张献忠起义军处决明瑞王朱常浩和他的随从以及巡抚陈士奇,惩办假称贫穷、隐瞒财富、为富不仁的豪绅地主;在成都,张献忠杀了明朝宗室,镇压妄图谋划反革命暴乱的儒生,还明令各地奴仆告发凶恶的主人,出现了翻身奴仆“恣意首告”[23],“戕灭其主,起而相应”[24]的生动景象。“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25]农民军的镇压行为,有哪些不正确的地方呢?“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26] 在反抗残酷暴虐封建统治者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在这么一场残酷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我们能责备农民军使用这个权威太多了吗?农民军绝不能、也没有采取“蠢猪式的仁义道德”[27],绝不能、也没有对敌对阶级施以仁政。正因如此,地主阶级对张献忠农民军恨之入骨,疯狂编造什么张献忠在四川“屠重庆”、“屠成都”、“屠士子”和“四路草杀”[28]的谣言。现代资产阶级自诩“公正客观”,但是他们在选用史料的时候,是本能地、顽固地站在了他们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故意摘取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诽谤之辞,坚持“张献忠屠川论”,同地主阶级一道对劳动人民极尽谩骂之能事,污蔑农民领袖和劳动人民,妄图达到否定造反有理,宣传革命有罪的罪恶目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文化喽啰就曾攻击“自赤祸糜烂蜀北,三年于兹,所过城市,再望为墟,屠戮之惨,胜于黄虎(指张献忠)。”[29]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是如此。他们发表攻击张献忠的言论、制作丑化张献忠的图片,是为了通过攻击张献忠是“杀人狂魔”、污蔑被压迫后奋起反抗的贫苦农民,来反毛反共人民,标榜只有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养尊处优的“精神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才有资格领导反对中修的“革命”。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右翼的恶性随机杀人事件,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派根本不同情被屠杀的群众,没有也不可能去分析清楚屠杀群众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翼的疯狂的法西斯心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修社会现状。他们只是将这些事件冠之以“献忠事件”这个词汇,心里唯有变态反动的幸灾乐祸的想法,唯恐中修不乱,把无辜群众的生命当成“加速”中修灭亡的燃料。如今,也有左圈分子喜欢“张献忠”梗,恬不知耻地在互联网上制作和传播丑化张献忠的文字、图片,发泄着他们阴暗刻毒的法西斯思想。——个人利益受损,那就要报复社会,搞一场屠杀。中国左圈主要是由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组成。这些被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不学无术、毫无政治原则,就这样“信了”张献忠屠杀的谣言,抑或明知是谣言,也要加以利用,乐此不疲地恶搞“张献忠”的梗,贬低高尚的革命领袖,为自己的法西斯反动思想辩护。
与“张献忠屠川”的谣言相联系的是有关“江口沉银”的谣言。在地主阶级的笔下,张献忠成了嗜杀成性、嗜财如命的刽子手,对待四川人民不仅屠杀,还要劫掠四川百姓的钱财。在满贼官修《明史》中,张献忠故意在锦江藏下巨额自己劫掠的钱财;《蜀难》等书,则是污蔑张献忠兵败船沉,船中藏着张献忠劫掠四川人民的钱财也一并沉入锦江。21世纪以来,中修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陆续发掘出明末蜀王、官僚地主的金银财宝,以及大西农民政权的货币和兵器,据称还有“四川百姓”所用的金银珠宝、生活用品。不少反动资产阶级分子认为这是张献忠劫掠“四川百姓”的罪证。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这种无耻谬论的人,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当时四川社会的真实情况。什么“四川百姓”有金银珠宝?况且,张献忠农民军一向保持着勤俭朴素的农民阶级本色,对金钱财货十分轻贱。每次作战缴获战利品时,“其金银恒散弃之”[30],张献忠也严禁士兵私匿金银,据记载,“藏银三两,既杀之”[31]。阴刻残忍、贪婪成性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特性,绝对不是贫苦农民的特性。杀人狂魔,只能是制造多次屠杀的满汉大地主、绝对不是农民领袖以及他所领导的农民军。毛主席曾说过:“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32]农民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不怕敌人污蔑、不怕敌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污蔑得再恶毒、反对得越厉害,越证明张献忠和他所领导的农民军的正确,越是证明革命的正确。
奢侈腐化还是艰苦朴素?
中修的喉舌常常以剥削阶级的道德来揣测劳动人民的品行,对于李自成领导的这支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起义军更是如此。他们毫无根据地胡说李自成的军队攻入京城后就“大肆掠夺金银珠宝”,“沉迷宫廷奢华与美色”,对百姓的剥削“比明朝更加深重”,致使起义最终失败。
中修的污蔑显然漏洞百出,李自成进京后并未立即完全清除城内的地主阶级复辟势力,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着召集私兵推翻新建立的农民革命政权。如果李自成起义军真的进京后奢侈腐化,甚至让城内百姓过得比明朝统治时期还要痛苦,那么这些复辟势力就能立即招募起大批私兵推翻新政权,农民起义军的政权就不会因为明朝军队与清军双重进攻下而灭亡,而是早就被城内的地主阶级政变成推翻。一个政权要想维持,必须要有一定的阶级支持它。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不同于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不是由地主阶级支持,而是由农民等劳动群众支持的。大顺农民军的战士们本身大多就出身于劳动人民,他们拿起武器反抗明朝封建统治是为了实现“均平”的革命纲领,消灭封建剥削。农民起义军本身来自农民,绝不会做出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正因如此,李自成起义才能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而接连击败明朝官军,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地主阶级向来对历代的农民起义恨得咬牙切齿,拼尽全力要绞杀起义,明朝的地主阶级自然也是时时刻刻妄图绞杀大顺农民政权,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农民军不能像大地主阶级一样可以依靠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和封建军队来勉强维持政权,他们能依靠的只有劳动群众,一旦失去劳动群众的支持,他们就会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更不用说在北京建立革命政权了。而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的行为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实已经能够证明。农民军进城后,继续执行严明的军纪,对人民秋毫无犯,对个别违反军纪的人立即处决,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后来,有不少市民与农民军成亲,也说明了群众与农民军关系亲密。不仅如此,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城后仍然保持农民简朴的作风,李自成本人就“早起,啜小米汤,惮用他物”[33] ,每天衣着朴素,早起,只喝小米稀粥,不吃其他东西。农民军的将领之间也以兄弟相称,同吃同坐,保持着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于城内的劳动人民,大顺农民军更是与他们保持着深刻的联系,李自成称起义军“专为救民”[34],曾两次在武英殿召见人民群众的代表,询问民间疾苦。他还把明朝宫廷“敬天法祖”的牌匾取下来,改为“敬天爱民”。而对以前祸害群众的宦官和大地主,则进行了严厉镇压,不仅勒令他们归还从人民身上剥削来的“赃物”,还将罪大恶极者驱逐出城,对明朝宫廷中三品以上的大臣,基本都不留用。在清算城内明朝大地主的同时,农民军也没有忘记全国各地明朝政府的残余势力,继续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刘宗敏就常常率军操练,李自成有时也会亲自检阅军队。正是在这样的训练下,农民军才能在进驻北京后接连攻下天津、山东等地,使大顺军控制的区域南邻江淮流域,北接长城沿线,东起沿海,西迄陕甘,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区域。如果农民军在北京时就奢侈腐化,宛若只知奸淫掳掠,一要打仗就落荒而逃的明朝军队一样,是绝对无法取得如此大的革命成果的。历代剥削阶级对农民军毫无根据的污蔑,完全在事实面前破了产。
毛主席曾指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5]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驳地主资产阶级的谬论,给予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正确的评价,并不是要给个别农民领袖树碑立传,而是要把颠倒的历史给颠倒回来,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真正的主人,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中修恰恰是最喜欢给地主阶级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中修如今大刮吹捧地主、贬低农民的黑风,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将资本家美化为天生就该统治人民的“有才能之人”,将广大劳动人民贬低为天生就该被统治的愚笨之人,从而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找寻“合理之处”。翻开中修的历史课本,中修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为了证明自身政权“合法性”,欺骗人民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要装模做样地承认一下“人民史观”、“人民创造历史”。中修本质上还是一个剥削阶级把持的政权,所以它又明里暗里抹黑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地主资产阶级称功颂德,还大力鼓吹本质是唯心史观的“多元史观”(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革命”史观,等等)。中修的历史教师,也对这一点心领神会,他们都是贬低群众、同时狂热地跪倒在剥削阶级脚下的哈巴狗、喉舌,向学生灌输英雄创造历史那一套黑货。中修会假惺惺地说:“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就是江山”……擦亮眼睛,准备斗争!识破中修剥削阶级的本质,不说抽象承认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空话,继续为农民以及广大人民翻案,彻底为农民以及广大人民翻案!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
习近平:《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 ↩︎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
程颢:《是游也得小松黄杨各四本植于公署之西窗戏作五绝呈邑令张寺丞·其三》 ↩︎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 ↩︎
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
转引自:河北师大政教系二年级四组:《李自成起义军横扫孔孟之道》,1975年02期《河北师大》。 ↩︎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梓潼县委宣传部和四川师范学院的同志曾作过实地调查,并作了一篇名为《把文昌帝君张亚子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文章。此处系根据他们的情况介绍。 ↩︎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彭孙贻:《平寇志》卷3。 ↩︎
佚名:《纪事略》。 ↩︎
汪楫:《崇祯长编》卷二。 ↩︎
光绪《射洪县志》卷十七《外纪》。 ↩︎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欧阳直:《蜀乱》。 ↩︎
同上 ↩︎
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一。 ↩︎
彭遵泗:《蜀碧》卷四。 ↩︎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
有关这四次屠杀的谣言,参见反动地主阶级分子查继佐所撰《罪惟录》、谢蕡所撰《后鉴录》等书。草杀,意即挨家挨户地杀,系反动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污蔑张献忠的言论。 ↩︎
民国重修《广元县志》卷二十《武备》。 ↩︎
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六。 ↩︎
毛泽东,转引自转引自冯清祥:《被敌人反对是好事》,1973年11月《人民日报》。 ↩︎
谈迁:《国椎》卷100。 ↩︎
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